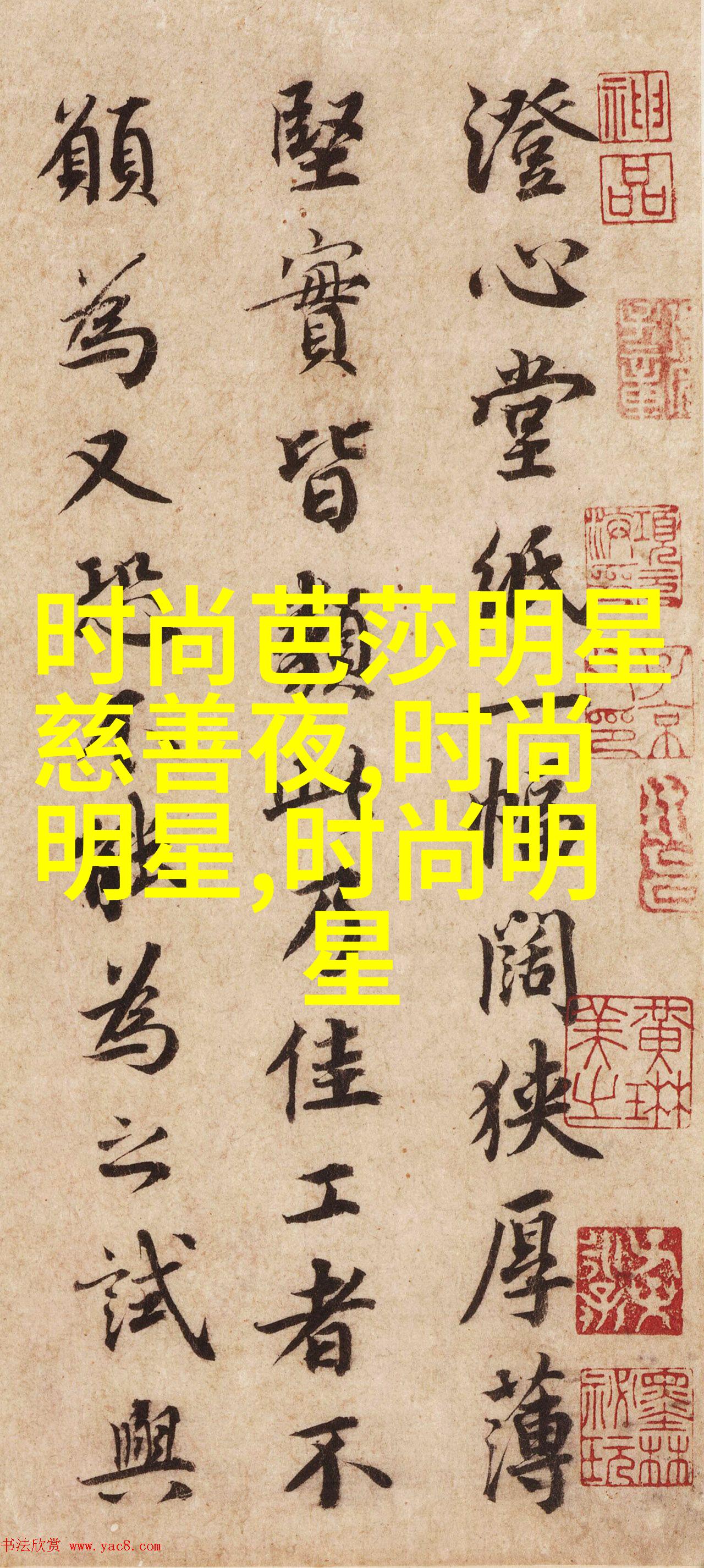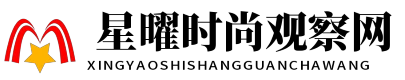我,许海峰,一名摄影记者,对朱钟华的作品深感好奇,上月在上海莫干山路创意园,他分享了他的最新作品,这是他近期集中展示的。观片会上,朱钟华展现的所有照片都是从上海街头拍摄的,黑白对比鲜明,有些画面处于盲拍状态,不仅失焦,还有变形和抖动,这种“填色”的感觉让我联想到幻象。在其他摄影师的黑白作品中,我并不常见到这种强烈的情感体验。这或许也是因为朱钟华镜头下的日常生活实在太过丰富多彩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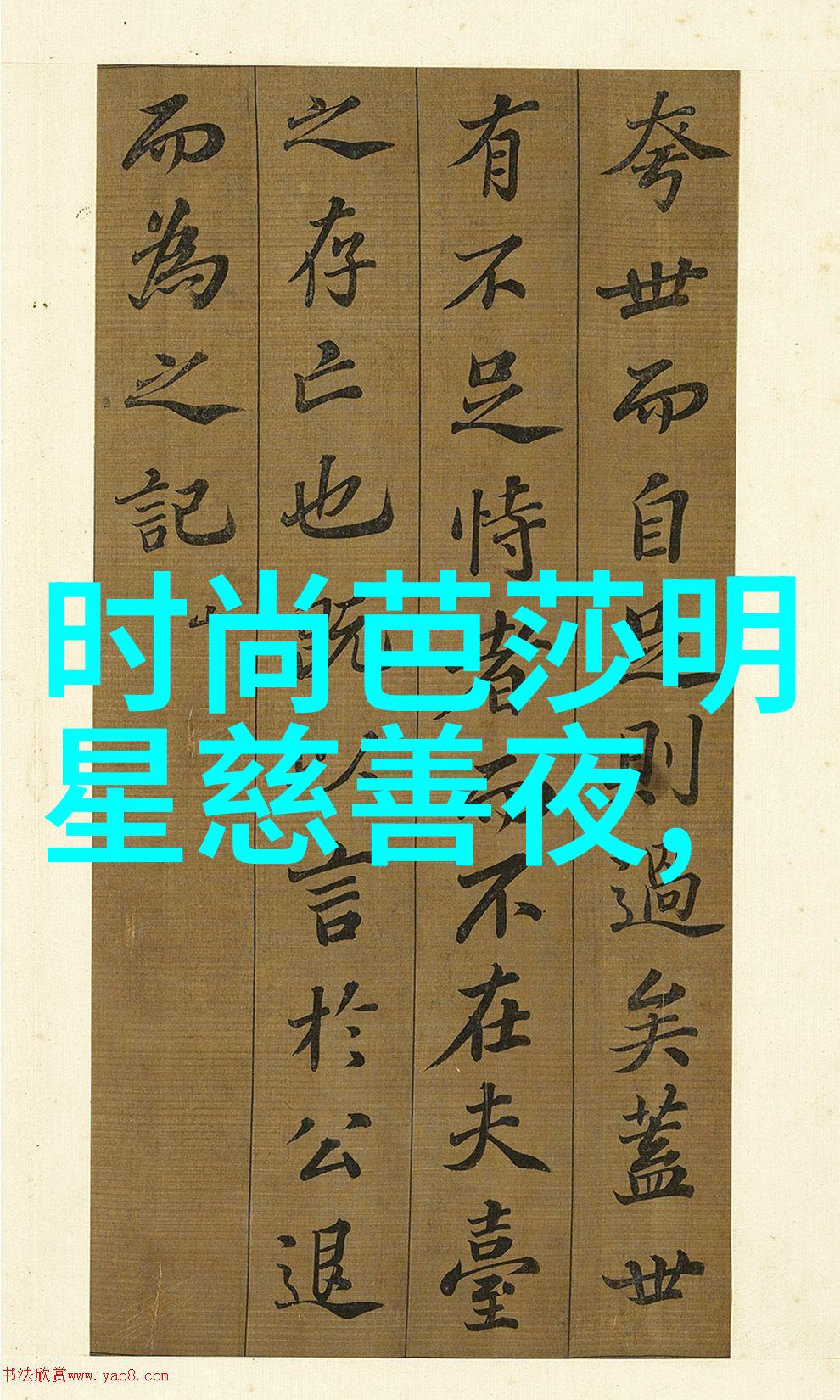
《时间的味道》这本书,在2018年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我注意到书中的许多照片都拍摄了不完整的人物线条。他解释说:“我在拍女人的时候,是拍她们的线条、局部、重要的是时代变化最先体现在女人身上。”同时,他也叮嘱我:“世界上最繁华的大街都是为女人的魅力服务的,你要记牢。”
通过他的镜头,我捕捉到了那份绚丽美,但又被他强行转换成黑白两色的画面,让读者沿着他预设的阅读轨迹前进。如果真的能做到心无旁骛,那就好了,可惜不行呀。朱钟华叮嘱我的,与他镜头下展示女性“美”,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一种“美”。他的“美”总是冷不丁地斜刺过来,让人猝不及防。

著名评论家林路老师在《时间的味道》序言中这样写道:朱钟华老道风格,用幽默视角捕捉现实,使得上海街头染上了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风韵,让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但是我看到这些评价后,不料朱老师直接回应:“我比较喜欢平淡无奇的地图,拒绝套路。”看完这里,我噗嗤笑出声来,朱老师真是越老越有趣。我想,这不是他故意与影评家作对,而可能是他的艺术求新求变之火奔突不息,然后他确实拍了很多质朴照片,以自证自己的立场,而好的照片就是没有火气、拒绝套路。
人是矛盾复杂体,当遇到像朱老师这样的非传统摄影师时,他们眼中的世界支离破碎。在顾铮笔下的金句中,“打破我们对于日常惯例式看法”的图像可以理解为他们在纪实与纪虚之间寻找动平衡点,以求突破和变异日常生活中的超拔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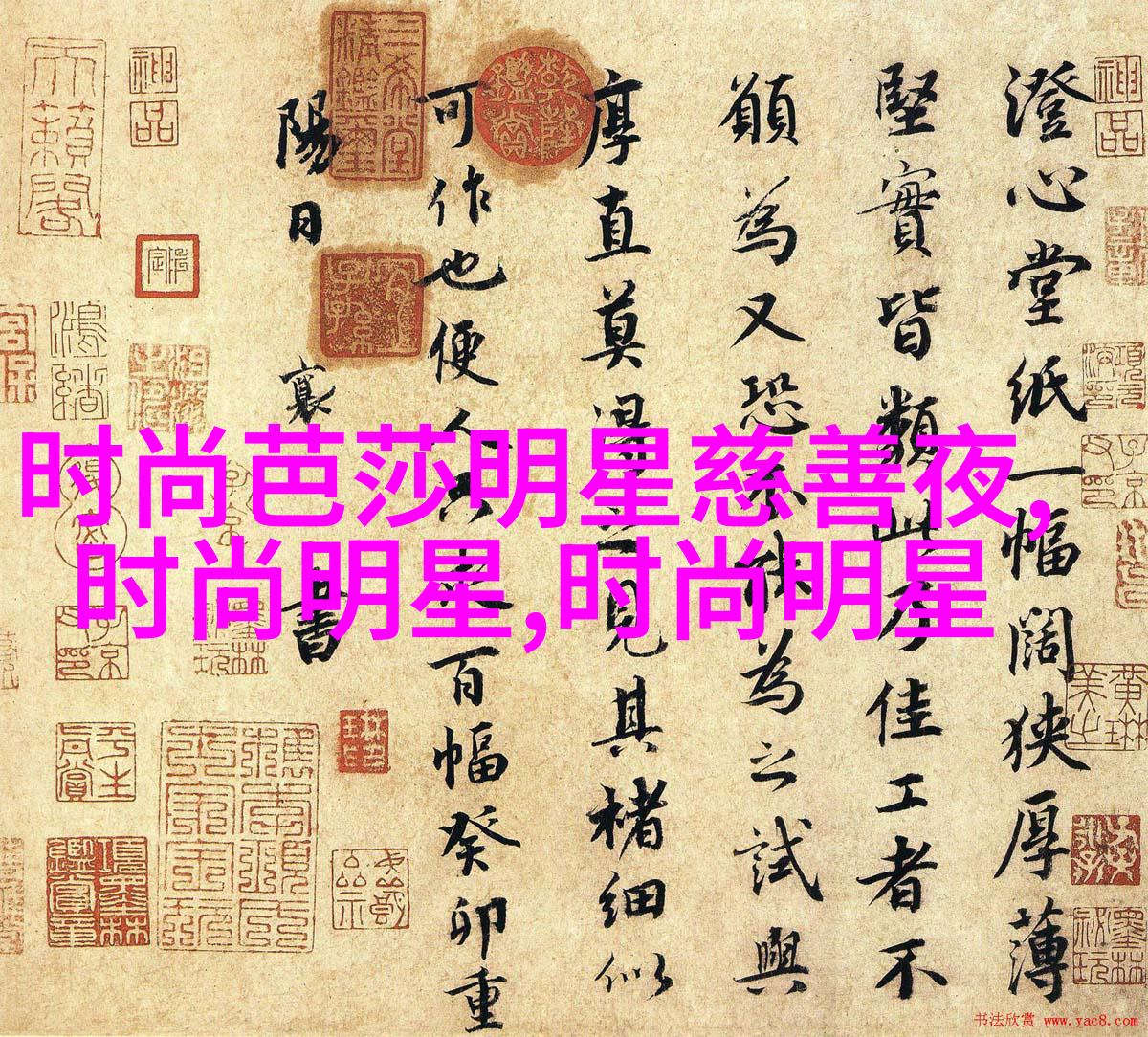
在这本画册里,他写下:我拍照,无为地取景…… 不需要纠结,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开枪,但心里蠢蠢欲动,只等待那一瞬间的心跳加速。这份创作方法和动机简洁而生动,透露出他的心思活动。某天清晨,我突然意识到,大多数照片中的被摄对象是在最紧张的一刻,就像是视频截图中漏掉不了的一瞬——快门按下太早错过,或太晚则真晚了。在被摄对象还未达到这一刻之前,他已经闻到了猎物正进入伏击圈,然后保持沉默,即使会迷惑对方伺机做出假动作以稳定对手。此时时间飞逝,空气凝固,一切千钧一发唯有释放快门截取滚动中的静帧才能救赎双方,这需要具备组织经营画面的能力,并自然赋予这一刻意义。这似乎与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决定性瞬间如出一辙,其实并不完全一样。
布勒松出现街头寻找几何形状,然后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在视觉中心点上必须丝毫都不差妙至巅毫精确。在决定性瞬间出现之前 布勒松应该长久观察地形光线机位人物走向等可能出现的情况以万无一失。而我们只能说布氏做事太规矩严谨属于那个时代需要这样一个人。而随着各种形式操弄把玩后的摄影,则努力打破一切规则这个时代。朱老师一上街就先放弃形式上的束缚,将大师们几何图形决定性的瞬间交还给大师然后走近被摄对象并迷惑对方(手持盲拍聊个天)。他也不回避追求妙至巅毫瞬间拖累截取流逝生命中的静帧以构成“时间之味”,更不会囿于主题先行意义所在让其截取下的静帧产生关联或本该无关联,由此得到舒展心态神色变得从容达到其所向往开放式意境表达也是一种思考创造力的赋予——准确地说,没有意义只是生活曾经如此发生过。这是他坚守且不断标榜也不变的事业追求简单而质朴。如果真以为这样简单,被蒙蔽了吧?